感谢关注耳机俱乐部网站,注册后有更多权限。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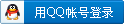
x
穆拉文斯基 在油管上看了一部记录片《Yevgeny Mravinsky: Soviet Conductor, RussianAristocrat》(叶夫根尼.穆拉文斯基:苏维埃指挥家,俄罗斯贵族)。一般音乐爱好者知道他,大概都是因为那套《柴可夫斯基四、五、六交响曲》,六十年代初出访西欧时的录音,在任何一个十大、百大唱片榜单上,大概都会有它一个位置。爆裂的柴六第一乐章,也是我大学失恋时反复聆听的一曲,铺天盖地而来的命运面前,个人是如此渺小、无助、绝望,只有无声地哀泣。想想,那会儿也是矫情!不过到底留下了病根,很少敢听那张唱片,只在架子上供着。 穆拉文斯基生于彼得堡贵族之家,革命前锦衣玉食,小时候的照片,就是天使的样貌。十月革命爆发,一家被赶进原来豪宅的一个房间居住,其它房间由无产阶级人民群众接收,第二年父亲熬不过去,抛下他母子俩离世而去,他们也无力再缴纳这一个房间的房租,只能搬出祖宅。整个就是一个现实版的《日瓦戈医生》。 不过,后来过得还算顺风顺水,读了音乐学院,加入了马林斯基剧院,三十年代,苏维埃把外国指挥家赶跑,年轻的芭蕾指挥被任命为列宁格勒爱乐乐团首席指挥,此后五十年指挥同一个乐团,熬过了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始终是苏维埃首席指挥家,万千恩宠。但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伴其一生,偷偷对太太说:“咱什么东西都不要攒,我不能再像1917年那样失去一切”。跟当局紧密合作却也保持距离,喝饱了伏特加,跟知己大提琴手嘟囔:“从某种意义上,你是幸运的,因为你没看到以前的俄罗斯是什么样子的…” 二战后,苏联和美国全方位竞争,从太空到深海都较着劲儿,音乐也不例外。老美火箭卫星失了先机,总结教训,据说其中一条是老毛子的文化艺术教育领先了。文学、绘画、电影啥的,其实两边处于不同的语境,没什么可比性。古典音乐就不一样了,评分系统一致。1958年冯.克莱本拿到了柴可夫斯基大赛钢琴组冠军,纽约万人空巷、纸带飘扬,迎接“征服了俄罗斯”的英雄归来。如斯盛况,空前绝后,从此再未出现在一个古典音乐家身上。苏维埃当然不能示弱,派出里赫特、奥伊斯特拉赫、穆拉文斯基等一干古典音乐精英访问西方,让腐朽的西方社会见识一下社会主义艺术的优越性。此等人物的天才、激情、痛苦,在社会高压体制下无处可去,唯有通过无言的音乐表达出来。现在看看,他们的艺术的深沉博大,似乎超越了在美国商业社会求生的那些音乐家,到底,西方社会虽有表达的自由,却无举国体制下对艺术的“无条件”支持。生存还是毁灭,在哪儿都是个问题。从这个角度观察,在政治高压下给予追逐金钱和知名度的自由,大概是一个社会可以对艺术施以的最大程度的毁灭性打击了吧? 但艺术是什么,难道不就是娱乐而已吗?戴假发的贵族在宫廷乐长的伴奏下,品着红酒,大嚼孔雀肝,和邻座的伯爵夫人调着情,所谓古典音乐,那会儿也不过是偷情前戏的背景音乐,但怎么就慢慢地变了味儿呢?1937年穆拉文斯基指挥肖斯塔科维奇《第五交响曲》的首演,列宁格勒的知识分子们群聚爱乐大厅,为“一个苏维埃艺术家对公正的批评的创造性回答”所震惊,继而全体起立欢呼不止时,也许他们知道,这是一个同类的垂死挣扎,或是面对枪口时的孑然独立。这里有任何娱乐性可言吗? 虽说所有的交响音乐都无法脱离作曲者的个人经历和历史语境,但老肖的音乐尤其如此。身边备着去古拉格用的牙刷毛巾小包,犯了“形式主义”错误的年轻作曲家写下了《第五交响曲》,辉煌吗?未必。但无标题的交响曲本就可以做各种各样的诠释,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起码有一个哈姆雷特能被主管意识形态的日丹诺夫批准,肖同志过了这一关,重新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音乐家。卫国战争爆发,老肖写下了英勇不屈(?)的《第七交响曲(列宁格勒)》,头戴消防员头盔的照片还上了《时代》杂志封面。但老肖永远是一个另类,在红军向着右岸乌克兰节节挺进,胜利喜讯不断传来的时候,穆拉文斯基指挥了老肖《第八交响曲》的首演,“悲悲戚戚”,人民不满意,斯大林同志不满意!穆拉文斯基面对文化主管部门的批评,再次演出《第五交响曲》,巨大的成功!他面对观众,高高举起总谱,犹如举着一幅圣像。这是他一生中,罕见的一次,对政权表现出艺术家的勇气。 在他被允许掌控的领域,穆拉文斯基是一个极端的完美主义者和典型的音乐暴君,一遍遍对细节的打磨,把他的团员练得死去活来。每次上台,他都得克服严重的舞台恐惧症,一次他的团员看到他在休息室里哭泣,问大师怎么了,原来他是在担心等一会儿演出时铜管进来得不整齐怎么办!他曾花了大量精力排练布鲁克纳《第七交响曲》,在最后一次正式排练的完整演奏中终于达到了他自己心目中的完美状态,但他立刻取消了演出,给出的理由倒也简单:“演出绝不可能达到刚刚这次排练的水平,你不可能把同样的事做两遍”。 纪录片中有一段是他排练舒伯特《第八交响曲(未完成)》,开头的一两个小节,乐团演奏了一遍,他就大摇其头:“没有节奏感,完全没有节奏感!”,这可是列宁格勒爱乐乐团在演奏一个不知演奏了多少遍的曲目!翻出他指挥的全曲唱片来听,倒没有很惊艳,大概是被太多的罐头音乐惯坏了耳朵吧?其实,我对第一次听《未完成》现场演奏的印象从没能在任何一张唱片中找到过:那是大学时学校业余交响乐团的一次排练,指挥是一位到访的前苏联指挥家。单簧管演奏员还是我同系同年级的一位女生,名字却忘记了,只记得她和木管组被指挥家单独练了好几遍。在我记忆中,这首曲子的鲜活印象就是二十五年前那个逼仄的排练厅,木管组各种各样的错音,以及天风海啸般的音响。
|